DIALOGUE┃我怎么就成了“保护伞”了?
序言
为介绍“打黑”、“扫黑”、“除恶”的相关法律实务问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李文涛律师结合办案心得,先后撰写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帽”是怎样炼成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司法认定标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司法认定标准及其变迁》、《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感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黑”回到解放前》、《我怎么就成了“恶势力”了(上篇)》、《我怎么就成了“恶势力”了(下篇)》系列文章,均刊发在“有效辩护”微信订阅号上。《我怎么就成了“保护伞”了》是上述文章定姐妹篇,也是“扫黑除恶破伞”专题的终结篇。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鼓励,欢迎朋友们对上述拙文一并拍砖、批评、指正。
前言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第二年。截止今年6月,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共5593个。与此同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结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4000多起,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00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1899人。可以预计,今明两年将有一大批“保护伞”案件陆续进入审判程序,进入公众视野。
刘某某是广州某区某派出所副所长,分管治安工作。2019年1月,该派出所辖区内一恶势力犯罪团伙落网,刘某随旋即受到牵连,因涉嫌受贿罪及“保护伞”受到监察调查,后被送往看守所羁押且不得取保。
一
问:我好端端的怎么就成“保护伞”了?
答:毕竟是干公安的哈,问题那么直接了当!
问:单刀直入不好吗?
答:好是好,只是三言两语答不好这个问题。
问:有那么复杂?
答:有那么复杂。
问:那就主意好!
问:从哪说起呢?
答:由简到繁,就从“保护伞”一词的词义和出处说起吧。
问:这些还需要说吗?
答:当然。尽管“保护伞”一词已成为妇孺皆知的高频词,但绝大多数人恐怕并不清楚它的出处和含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意吧?
问:同意。
答:你自己也大抵如此吧?
问:确实。
答:身为派出所副所长尚且如此,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可见,“保护伞”问题看似简单,却内有乾坤。这个问题说透了,你自然就明白你怎么就成“保护伞”了,就怕你没有这个耐心。
问:我都被打成“保护伞”了,还能没有这个耐心吗?
答:有就好!不过⋯
问:不过什么?
答:不过首先得纠正你一下:你的案子目前还处在侦查阶段,你现在只是“涉嫌”充当“保护伞”,但还没有被“打成”“保护伞”。你是不是“保护伞”、是哪一类“保护伞”,还得经人民法院审理后才能定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你应该清楚啊!
问:你说的是“法院定罪原则”吧?
答:行家啊!一点就通!
问:毕竟是干公安的,这点常识总得有吧?
答:有就好!这样聊起来就省事多了。
问:那我就洗耳恭听了?
答:你也别光洗耳恭听!
问:为什么?
答:你干公安,我干律师,虽说同属法律共同体,所依法律相同,但你我角色不一样,关注点就不大一样,关注点不一样,知识面就不大一样。我不清楚哪些问题你已知晓,哪些问题你还又疑惑。所以,还是你问我答吧。
问:这就开始吗?
答:这就开始吧。
问:“保护伞”就是一个比喻吧?
答:是的。“保护伞”就是一个比喻,指一切可以起庇护作用的力量,可以是国家、组织、机构或个人。
问:比如说?
答:比如说,你作为一家之主,庇护着你的父母、妻子、子女,那就可以说,你是你家人的“保护伞”。
问:这个比喻好!又比如说?
答:比如说,你身为派出所副所长,爱岗敬业,正义凛然,保一方平安,那就可以说,你就是本辖区居民的“保护伞”。
问:这个比喻也很好!再比如说?
答:比如说,你身为派出所副所长,正不压邪,非但不保一方平安,反与不法分子沆瀣一气,那就可以说,你是本辖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问:这个嘛⋯这么说,“保护伞”其实本无褒贬之分?
答:话锋转得挺快哈!是的,“保护伞”本是一个中性词,其褒贬取决于保护了谁:保护了好人,就是一把“好伞”,是褒义词;保护了坏人,就是一把“坏伞”,是贬义词。
问:我这次被抓,肯定就是一把“坏伞”咯?
答:再次重申,你是不是“保护伞”、是哪一把“保护伞”,得经法院审理后才能定论,怎么又问起这个?
问:我这不是着急嘛!
答:现在着急有用吗?
问: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
答:不过什么?
问:如果我的问题太简单,不能笑话我弱智。
答:只有不懂的问题,哪有什么简单的问题!
问:“保护伞”一词出自《刑法》吗?
答:错。我国《刑法》从未使用过“保护伞”一词。
问:那就是出自《刑诉法》咯?
答:错。我国《刑诉法》也从未使用过“保护伞”一词。
问:既如此,那“保护伞”就不是个刑事概念咯?
答:错。尽管“保护伞”一词既非出自刑法,也非出自刑诉法,但它又的的确确是个刑事概念。
问:晕!成心绕我?
答:绝非成心绕你,确实如此。
问:咋讲?
答:因为“保护伞”一词就源自刑事政策文件、刑事司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且已在涉黑涉恶案件的裁判文书中被广泛使用。可以说,“保护伞”既是一个刑事政策概念,又是一个刑事司法概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刑事概念。这么说没毛病吧?
问:没毛病。只是⋯
答:只是什么?
问:只是以前光顾着抓人,哪知道现在反被抓啊?!因此,以前确实没有太关注这些法律文件。
答: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问:虽说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趁此机会恶补一下。
答:义不容辞,我是你的辩护律师嘛!
问:可以捋一捋“保护伞”一词的来龙去脉吗?
答:可以。这得从黑社会性质组织说起,因为“保护伞”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
问:确实。
答:1997年《刑法》第294条创设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并未具体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吧?
问:是的。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率先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保护伞”特征、非法控制特征,是吧?
问:是的。“保护伞”一词就源自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吧?
答:错。
问:错?你不是说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特征吗?
答:我是这么说的。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问:咋讲?
答:尽管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率先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特征,但并没有使用“保护伞”一词。
问:规定了“保护伞”特征,却没有使用“保护伞”一词!听起来咋那么玄乎啊?蒙我?
答:一点不玄乎,也绝非蒙你。因为“保护伞”特征只是专家学者和司法人员对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即: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的形象概括。正是基于这个规定,当时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之间的关系被界定为共存关系。
问:共存关系?
答:是的。根据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涉案组织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它背后就必然存在一把(或多把)“保护伞”。简言之,“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必有‘保护伞’”。
问:反之亦然?“有‘保护伞’就必有黑社会性质组织”?
答:错。因为“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必有‘保护伞’”和“有‘保护伞’就必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两个严谨的互逆定理。
问:为何强调“严谨”?
答:原因很多,只讲二个。
问:其一?
答:首先,是因为理论与实践存在“两张皮”现象。
问:怎么个“两张皮”法?
答:根据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特征,才能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缺一不可。
问:就像打麻将,“三缺一”就打不成了?
答:是的。即使涉案组织具备“保护伞”特征(即存在“保护伞”),如果不具备其他三个基本特征,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问:易言之,“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必有‘保护伞’”与“有‘保护伞’就必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理论上不构成互逆定理?
答:正是。
问:司法实践上呢?
答:当时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有‘保护伞’就必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又导致了两种错误做法:一是为了“破伞”而降格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二是为了“打黑”而降格认定“保护伞”。这就使得“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必有‘保护伞’”与“有‘保护伞’就必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际上被错误地“互逆”了。
问:一针见血!其二呢?
答:其次,是因为“保护伞”一词的多义性。
问:咋讲?
答:“保护伞”一词,时而呈现出法律性,时而呈现出政策性,时而呈现出政治性,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错落各不同。语境不同,内涵就不同;内涵不同,“保护伞”的类型就不同。这正是“打/扫黑除恶”背景下“保护伞”问题的奇特之处。
问:“保护伞”还有分类?
答:当然有。“保护伞”分类是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在此按下不表,还是先回到“保护伞”一词的出处吧。
问:好。(尴尬)刚才聊到哪了?
答:刚才谈到,虽然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率先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特征,但并未使用“保护伞”一词。
问:对对对。那“保护伞”一词究竟从何而来?
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基本特征修改为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是吧?
问:是吗?与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区别吗?
答:当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不再把“保护伞”特征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独立特征,而是将“保护伞”因素巧妙地规定在非法控制特征之中,把“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非法控制的手段之一。
问: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有啥区别?
答:区别大了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实际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将“保护伞”特征做了降格处理,不再把“保护伞”特征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独立特征,使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的关系从共存关系降格为或有关系。
问:哪又怎样?
答:这一变化,巧妙化解了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必有‘保护伞’”(反言之:“有‘保护伞’才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制度设计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困境,既降低了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门槛,又保持对“保护伞”继续吊打,既有利于从严“打黑”,又有利于“破伞”的宏观调控,可谓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关系的难题,使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的关系更具弹性,从而使“打黑”和“破伞”变得更加可控,进可攻、退可守,更加富有战略弹性。
问:干得漂亮!
答:是说我吗?
问:呵呵,我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干得漂亮。
答:确实漂亮。
问:怎么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之间的“或有关系”?
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的规定,即使没有“保护伞”因素(即不存在“保护伞”),涉案组织也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简言之,“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未必有‘保护伞’”。
问:“保护伞”一词就源自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吧?
答:错。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保留了“保护伞”因素,但同样没有使用“保护伞”一词。
问:听起来咋那么绕啊?又蒙我?
答:一点不绕,也绝非蒙你。“保护伞”同样是专家学者和司法人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即: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中“保护伞”要素的形象概括。
问:“保护伞”一词到2002年4月都没有在正式文件中出现?
答:至少在公开的法律文件没有。至于未公开的“内部文件”是否使用就不得而知、也无关紧要,毕竟这种“内部文件”登不了刑事诉讼的大雅之堂。
问:那“保护伞”一词何时才登上刑事诉讼的大雅之堂呢?
答:很快。2002年5月1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和<关于刑法第384条第一款的解释>的通知》(以下简称最高检2002年《通知》)就率先直接使用了“保护伞”一词(《通知》第二条[节选]: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即是否要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或者为犯罪活动提供非法保护,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对于同时具备《解释》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的案件,应依法予以严惩,以体现“打早打小”的立法精神。同时,对于确有“保护伞”的案件,也要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问:奇怪,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文件呢?
答:这并不奇怪,毕竟你是干公安的,不是干检察的,而率先使用“保护伞”一词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是公安部。
问:谢谢安慰!从此,“保护伞”一词就成为了正式的官方用语?
答:是的。从那以后,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最高法《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和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都先后使用了“保护伞”一词。你不会告诉我,这些文件你也不知道吧?
问:那倒不至于。2018年初我们公安系统还专门组织学习了党中央国务院2018年《通知》,后面两个文件也组织过内部学习,毕竟是公安部联合发文的嘛。只是⋯
答:只是什么?
问:只是当时更关注“扫黑除恶”问题,不大关注“保护伞”问题。
答:为什么?
问:觉得自己离“保护伞”很遥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答:现在还这么想吗?
问:扫黑也好,除恶也罢,现在已经没有我什么事了,现在我只想把“保护伞”问题整个明白。
答:好,那我们就接着聊。
二
问:你刚才说,“保护伞”有不同分类?
答:是的。
问:分哪几类?
答:在“打/扫黑除恶”的语境下,“保护伞”可分为狭义“保护伞”和广义“保护伞”二大类。
问:怎么界定狭义“保护伞”呢?
答:狭义“保护伞”是刑法意义上的“保护伞”,特指实施了《刑法》第294条第三款(《刑法修正案(八)》之前为《刑法》第294条第四款,下同)规定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人。简言之,谁实施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谁就是狭义“保护伞”。
问:能否说,谁包庇、纵容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谁就是狭义“保护伞”呢?
答:不能。因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不等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前者是上位概念,后者是下位概念,两者不能划等号。简言之,只要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构成了“保护伞”,至于是狭义“保护伞”还是广义“保护伞”,取决于对“包庇、纵容”做狭义解释还是作广义解释。
问:对“包庇、纵容”作狭义解释,就对应狭义“保护伞”,作广义解释,就对应广义“保护伞”?
答:正是。
问:怎么定义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呢?
答:《刑法》第294条第三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就构成本罪。
问:可以称之为“保护伞罪”吗?
答:尽管“保护伞罪”不是一个规范罪名,倒也形象生动,且便于与广义“保护伞”相区别。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就权且这么称谓吧。
问:“保护伞罪”中既有“包庇”、又有“纵容”,究竟是一个罪名还是两个罪名?
答:这是一个选择性罪名,包括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问:可以分别称为“包庇伞罪”和“纵容伞罪”吗?
答:尽管这也不是规范罪名,但如果这样命名可以加深你的理解,也未尝不可。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就权且这么称谓吧。
问:“包庇伞罪”和“纵容伞罪”能否数罪并罚呢?
答:不能。这是由选择性罪名的特征决定的:如果行为只构成“包庇伞罪”或“纵容伞罪”,就只能认定一罪;如果行为同时构成“包庇伞罪”和“纵容伞罪”,就只能认定为“保护伞罪”,不再分别认定“包庇伞罪”和“纵容伞罪”。无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都属于实质的一罪,不会数罪并罚。
问:“保护伞罪”的法定刑重吗?
答:构成本罪的,2011年之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2011年之后,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问:就是说,构成本罪,2011年之前,法定刑最低是剥夺政治权利,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2011年之后,法定刑最低是六个月有期徒刑,最高是十五年有期徒刑?
答:正是。
问:2011年后,这法定刑为啥就蹭蹭往上窜啊?
答:你说还能为啥?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干掉狭义“保护伞”咯。
问:恐怖!
答:那以你为啊!
问:但愿我不属于狭义“保护伞”!
答:同愿。
问:“保护伞罪”一律由公安机关管辖吗?
答:是的。
问:为何不是由监察机关管辖呢?
答:好问题!“保护伞罪”本质上属于职务犯罪,按法定管辖权制度,理应由监察机关(之前为检察机关)管辖,但实际上却由公安机关管辖。这种管辖安排受到质疑和诟病,理由之一是有“护犊子”之嫌。
问:咋讲?
答:这不明摆着嘛!理论上,虽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能涉嫌“保护伞罪”,但实践中公安警察涉嫌“保护伞罪”可能性更大、机会更多,却是不争事实。因此,由公安机关管辖“保护伞罪”案件,难免使人产生“一家人关起门来说话”的遐想,即便再有公心,也难逃“护犊子”之嫌。
问:既然是“护犊子”,怎么就不护护我?我也是公安警察嘛,怎么把我当“保护伞”送进来了呢?
答:客观地说,把你当“保护伞”送进来,与这种管辖安排无关,而是与“扫黑除恶”的大局有关,是大势所趋。可以说,如果不是这种管辖安排,恐怕你早就进来了。再者,你也不一定构成“保护伞罪”呢!
问:罢了罢了。怎样才算构成“保护伞罪”呢?
答:“保护伞罪”是一个选择性罪名,包括“包庇伞罪”和“纵容伞罪”,两者虽然法定刑相同,但犯罪主体、目的、行为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分开来说或许更容易讲明白。
问:那就先说说“包庇伞罪”?
答:甚好。把“包庇伞罪”整明白了,“纵容伞罪”就基本上整明白了。
问:“包庇伞罪”中的“包庇”想必是作狭义解释吧?
答:正是。
问:具体是怎样规定的呢?
答: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包庇伞罪”中的“包庇”,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实施的下列行为:1、通风报信,2、隐匿、毁灭、伪造证据,3、阻止他人作证、检举揭发,4、指使他人作伪证,5、帮助逃匿,6、阻挠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禁,7、其他。
问:只要实施了这七种行为之一就算“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
答:错。
问:错哪?
答:错在理解不全面。因为只有出于“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这一特定目的(以下简称“包庇目的”),同时又实施了这七种行为(以下简称“包庇行为”)之一,才算“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简言之,包庇目的和包庇行为,一个都不能少。
问:易言之,如非出于包庇目的,即使实施了包庇行为,也不算“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
答:正是。
问:能否说,如非出于包庇目的,即使实施了包庇行为,也不构成犯罪?
答:不能。因为在你给定的情形下,只能说不构成“包庇伞罪”,但不能说一概不构成犯罪。易言之,这种情形虽不构成此罪,但可构成彼罪,因为“包庇”本身就涉嫌犯罪。
问:比如说?
答:比如说,包庇行为可能构成下列犯罪:伪证罪(《刑法》第305条),妨害作证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第307条),窝藏、包庇罪(《刑法》第310条),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或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刑法》第349条),徇私枉法罪(《刑法》第399条)。
问:如果包庇行为构成了“包庇伞罪”,能否同时构成上列犯罪?能否数罪并罚?
答:不能。因为“包庇伞罪”与上列罪名之间是法条竟合关系,应当按“特别法由于普通法”原则处理,只能认定一罪,不能认定数罪,不能数罪并罚。因此,如果认定了“包庇伞罪”,就不能同时认定上列罪名。反之亦然。
问:“包庇伞罪”与上列罪名有何区别?
答:区别多了去了!
问:比如说?
答:比如说,犯罪分类不尽相同,犯罪主体不尽相同,犯罪客体不尽相同,犯罪行为不尽相同。但这些都不是最本质区别。
问:那最本质区别是什么?
答:对象。
问:对象?
答:是的,对象!即使包庇行为相同,如果包庇对象不同,触犯的罪名也不相同。根据《刑法》第294条第三款和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包庇伞罪”的包庇对象仅限于两类,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二是境外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除有特别说明外,以下在讨论“包庇伞罪”的包庇对象时,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指代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境外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
问:既如此,那为什么不称为“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境外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罪”呢?
答:有才!
问:扁我?
答:非也。你起的这个罪名的确更加准确无误,但是⋯
问:但是什么?
答:但是有失冗长。
问:咋讲?
答:其一,法律用语除要求准确无误外,还要求符合经济原则。根据常识,组织与成员是依存关系,有成员才有组织,有组织就有成员。既如此,包庇了组织,也就包庇了成员,反之亦然。因此,将“包庇伞罪”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解释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既符合常情常理,又符合《刑法》第294条第三款的立法本意,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
其二,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雏型,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显然轻于后者。根据常识,既然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构成犯罪,那么,包庇境外黑社会组织(我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组织)就更应当构成犯罪。因此,将“包庇伞罪”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解释为包括“境外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既符合常情常理,又符合《刑法》第294条第三款的立法本意,同样能为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
可见,“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一规范罪名,既符合了准确无误要求,又符合了经济原则。
问:根据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第五条,包庇目的+包庇行为+包庇对象=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下总算对了吧?
答:对+牛。
问:为何要+牛?
答:你用数学公式表达法律问题,简单明了,因此要+牛!
问:包庇目的+包庇行为+包庇对象=“包庇伞罪”?
答:错。包庇目的+包庇行为+包庇对象只是构成“包庇罪”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
问:那构成“包庇伞罪”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答:套用你的公式,构成本罪的充分条件可大致表示为:包庇主体+包庇故意+包庇目的+包庇行为+包庇对象≈“包庇伞罪”。
问:为何用约等号?
答:原因有二。
问:其一?
答:其一,即使具备了上述五个要件,但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不认为是犯罪,就可以不定罪处罚。
问:你说的是《刑法》第13条的“但书”吧?
答:正是。
问:其二?
答:其二,与实施“包庇伞罪”是否必须“利用职务便利”有关。
问:咋讲?
答:尽管两高两部2018年《指导意见》认定“利用职务便利”不是本罪的必备要件,只把“利用职务便利”作为本罪的从重处罚情节来对待(《刑法》第294条第三款中规定的“包庇”行为,不要求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利用职务便利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酌情从重处罚),而且从2018年起实践中也这么操作,但这一规定是否符合《刑法》第294条第三款的立法本意、罪刑法定原则及职务犯罪原理,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务上,都仍然值得商榷。
问:何以见得?
答:说来话长。
问:简单说说?
答:简单说说。《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无非是两大类型:一是“滥权”型,二是“失职”型(“徇私”只是滥权或渎职的动机,不属单独一类),是吧?
问:是的。
答:“滥权”意为滥用职权,“失职”意为玩忽职守,两者都以公职、公权力为依托,离开公职、公权力,就无所谓“滥权”或“失职”,是吧?
问:是的。可否这么说:没有职务,就没有职务行为,没有职务行为,就没有公权力行使,没有公权力行使,就没有滥权或失职,没有滥权或失职,就没有职务犯罪,因此,职务犯罪无一例外都利用了职务便利?
答:归纳得还行,但是⋯
问:但是什么?
答:但是只说对了一半。你可以说,“滥权”型职务犯罪无一例外地利用了职务便利,但你不能说,“失职”型职务犯罪无一例外地利用了职务便利。
问:咋讲?
答:因为“滥权”型职务犯罪表现为滥用职权,不应当作为而乱作为,属于积极的、作为的职务犯罪,因此,必然“利用职务便利”。而“失职”型职务犯罪表现为玩忽职守,应当作为而不作为,属于消极的、不作为的职务犯罪,因此,无需“利用职务便利”。
问:“包庇伞罪”属于“滥权”型职务犯罪吗?
答:“包庇伞罪”属于积极的、作为的职务犯罪,当属“滥权”型职务犯罪。
问:可见,你不认同两高两部2018年《指导意见》的上述规定?
答:是的。
问:为何?
答:理由有六。其一、“包庇伞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当属职务犯罪,应符合职务犯罪原理。其二、“包庇伞罪”属“滥权”型职务犯罪,必然“利用职务便利”。其三、《刑法》第294条第三款虽未明说,但无论是文义解释还是系统解释,都可解释为包含了“利用职务便利”的内在要求。其四、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就与普通人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无异,而普通人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构成“包庇伞罪”(但可能构成《刑法》第310条规定的包庇罪)。其五、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其行为与《刑法》第310条规定的包庇罪的犯罪构成更加吻合,认定为包庇罪更为妥当(包庇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普通人,也可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六,即便“包庇伞罪”与包庇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但由于上述第三个理由,“特别法由于普通法”原则在此并不适用。
问:言之有理。这也是你的一家之言吗?
答:当然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就认为,“包庇伞罪”中的包庇行为“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张明楷《刑法学(下)》,第1073页,法律出版社,第五版)。
问:感谢张明楷教授,为“包庇伞”们说了一句公道话!
答:同感。
问:如此说来,两高两部2018年《指导意见》实际上降低了“包庇伞罪”的入罪门槛吧?
答:正是。
问:这是不是有点任性啊?
答:呵呵。
问:也罢。你刚才说,“包庇伞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答:是的。更确切地说,“包庇伞罪”的犯罪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知道,是指在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监察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哪些人又属于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
答:四类人。
问:第一类?
答: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属此类。
问:第二类?
答: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文化局委托的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卫生局委托的卫生防疫站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属此类。
问:第三类?
答: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比如说,公安机关临时聘用的辅警、城管机关临时聘用的辅管即属此类。
问:第四类?
答: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问:在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属于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构成“包庇伞罪”?
答:是的。
问:有此类案例吗?
答:有。根据国家监察委的官宣,桂林市永福县政协原主席刘永祥,就因构成“包庇伞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最终被判处了十四年有期徒刑。
问:“包庇伞罪”都是故意犯罪吗?
答:是的。过失不构成本罪。
问:怎样才算有“包庇故意”呢?
答: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得提一提“故意犯罪”这个概念。
问:我略知一二哦。
答:说说看。
问:好。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中的“故意”,在结果犯的情形下,是对危害结果的故意,属结果明知;在行为犯的情形下,是对危害行为的故意,属行为明知。对吧?
答:知道得不少啊!
问:惭愧惭愧。
答:那包庇故意中的认识因素是结果明知还是行为明知?
问:这个⋯
答:哪个?
问:这个⋯这个还是你说吧!
答:既非结果明知,也非行为明知,而是对象明知。
问:啊?
答:刚说过,“包庇伞罪”的包庇对象仅限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吧?
问:是的。你还说在讨论包庇对象时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指代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境外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可那又如何?
答:那就说明,只有行为人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仍然予以包庇,才构成“包庇伞罪”。反言之,如果行为人不明知其所包庇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使明知其所包庇的是其他犯罪组织及其成员,也不构成“包庇伞罪”(但不排除构成窝藏包庇罪或其他包庇类犯罪的可能性),这完全符合“不知者不罪”这个古老而朴素的道理。可见,包庇故意的认识因素当属对象明知。当然,这里所说的“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所包庇的可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不要求行为人像司法人员那样确切地认识到其包庇的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问:这是你一家之言吗?
答:当然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就认为,如果行为人应当认识到其所包庇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没有认识到的,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明知,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包庇故意,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张明楷《刑法学(下)》,第1073页,法律出版社,第五版)。
问:张教授这个观点超好!超赞!
答:同赞。
问:司法实践也持这个观点吗?
答:2009年之前这是通说,2009年后通说被否定了。
问:啊?!
答:还记得上面提及的两高一部2009年《座谈会纪要》吧?
问:记得。
答:两高一部2009年《座谈会纪要》一方面强调,“包庇伞罪”必须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但另一方面又规定,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仍对该组织及其成员予以包庇,即可认定本罪,至于行为人是否明知该组织系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问:这不就意味着,包庇故意中的认识因素既可以是事实明知,又可以是推定明知吗?
答:是的。
问:这不就意味着大大降低了“包庇伞罪”的入罪门槛吗?
答:是的。
问:这有问题啊!
答:啥问题?
问:问题多多,只说其二。其一,不符合“不知者不罪”这个古老朴素的道理。其二,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而予以包庇,顶多定个包庇罪嘛,怎能定“包庇伞罪”呢?实践中,如果这个“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没有被追诉,或者虽然被追诉但没有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行为人构成“包庇伞罪”岂不是霸王硬上弓?岂不荒谬?果真如此,咋办?
答:凉拌。
问:凉拌?!
答:开个玩笑。理论上,你担心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几率不大。
问:咋讲?
答:你想啊,司法人员又不是吃素的,他们当然清楚“包庇伞罪”的包庇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避免出现你担心的情况,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会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本罪同时立案、同时侦查,并尽可能同时移送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会对两个案件同时审查,并尽可能同时起诉。在审理阶段,法院会采用延时判决的策略,先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件做出判决,后对本罪案件做出判决:如果在先判决是有罪判决,在后判决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定“包庇伞罪”,反之,如果在先判决是无罪判决,在后判决就不会认定“包庇伞罪”。如此,程序上既贯彻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保护伞”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实体上又尽可能准确认定“包庇伞罪”,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你担心的实践困境。
问:照这么说,我是纯属咸吃萝卜淡操心咯?
答:我没这么说,但同意你的观点。
问:呵呵。关于“包庇伞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答:大哥,不是我还有什么要说,而是你还有什么要问。
问:我基本明白了,不问了。
答:我基本讲完了,不说了。
问:那就开始聊“纵容伞罪”?
答:OK。
三
问:“纵容伞罪”中的“纵容”,想必也是作狭义解释吧?
答:是的。
问:具体是怎样解释呢?
答: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纵容伞罪”中的“纵容”,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可见,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问:“不依法履行职责”包括不履行和不认真履行,是吧?
答:是的。
问:其实就是玩忽职守,是吧?
答:是的。
问:用“放纵”解释“纵容”,这不就是同义反复么?
答:确实。
问:这也算是解释?
答:算。不但算,而且这也是至今为止最高司法机关对“纵容伞罪”中的“纵容”所作的唯一一次官方解释。
问:怎么定义“纵容伞罪”呢?
答:这个简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就构成本罪。
问:即如此,“纵容伞罪”的充分条件可否表示为:纵容主体+纵容故意+纵容目的+纵容行为+纵容对象≈“纵容伞罪”?
答:错。
问:错哪了?
答:错在多了“纵容目的”。与“包庇伞罪”不同,“纵容伞罪”只需具备纵容故意,不需具备纵容目的。
问:那可否表示为:纵容主体+纵容故意+纵容行为+纵容对象≈“纵容伞罪”?
答:又错。
问:又错哪了?
答:错在用了约等号。
问:你上面不也用约等号了吗?
答:上面可以用,这里不能用。
问: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答:非也。如上所述,“纵容伞罪”属于“失职”型职务犯罪,无需“利用职务之便”,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是否本罪的构成要件的分歧。既如此,“利用职务便利”就不是本罪的一个或有因素,既然不是本罪的一个或有因素,就不是公式中的一个变量,因此,应当用等号,而非约等号。
问:so that s ne!那就表示为:纵容主体+纵容故意+纵容行为+纵容对象=“纵容伞罪”?
答:有才。
问:谬赞。纵容主体与包庇主体的范围相同吧?都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吧?
答:错。“包庇伞罪”和“纵容伞罪”虽然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但两者的犯罪主体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问:咋讲?
答:根据《刑法》294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仅从字面上看,两者的犯罪主体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相同之处。但从实质上看,前者的犯罪主体范围远大于后者:前者的犯罪主体包括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同),后者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负有法定查禁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不同之处。
问:可否表示为:包庇主体范围>纵容主体范围?
答:可以。
问:哪些人属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负有法定查禁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
答:大哥,你是老警察,这个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问:我说说看?
答:洗耳恭听。
问:人民警察当属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负有法定查禁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属纵容主体,对吧?
答:错了。
问:错哪?
答:错在以偏概全。根据《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可分为五大类,即公安机关的公安警察、国安机关的国安警察、监狱机关的监狱警察、劳动教养机关的劳教警察以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随着劳教制度于2013年被废除,劳教警察不复存在,因此,人民警察现在只有四大类)。其中,国安警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家安全,监狱警察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刑事处罚,司法警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诉讼秩序,他们并没有查禁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因此,他们可以成为“包庇主体”,但不属于“纵容主体”。当然,如果他们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线索,就有义务将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如果应当移交而拒不移交的,就可构成“包庇伞罪”或其他的职务犯罪,但不构成“纵容伞罪”。由此可见,不能说凡是人民警察都负有查禁黑社会性质组织违反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都属于“纵容主体”。
问:言之有理。公安警察当属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负有法定查禁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属纵容主体,这样说总没错了吧?
答:又错。
问:错哪?
答:还是错在以偏概全!尽管《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公安警察的十四项职责中的第一项就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但公安警察又可以细分为治安警察、刑事警察、经济警察、缉私警察、缉毒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巡逻警察、林业警察、铁路警察、航运警察等警种,不同警种承担不同的法定职责,并非每个警种都直接承担“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更非每个警种都直接承担查禁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其中,治安警察、刑事警察不但直接承担“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而且根据上述“保护伞罪”案件的管辖安排,还直接承担查禁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因此,他们当属“纵容伞罪”的适格主体。当然,其他警种在履行本职工作时发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有义务将线索移交其他警种处理,如果应当移交拒不移交的,可构成“包庇伞罪”或其他职务犯罪,但不构成“纵容伞罪”。由此可见,也不能说凡是公安警察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反犯罪活动负有法定查禁职责、都属于“纵容主体”。
问:确实如此。除了治安警察、刑事警察外,还有哪些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负有法定查禁职责呢?
答:这取决于对“查禁职责”是作狭义解释还是作广义解释。
问:如果对“查禁职责”作狭义解释呢?
答:所谓狭义的“查禁职责”是指法定的查禁职责。如果对“查禁职责”作狭义解释,除治安警察、刑事警察外,我确实想不出还有哪些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负有法定查禁职责。
问:如果对“查禁职责”作广义解释呢?
答:所谓广义的“查禁职责”是指政策性的查禁职责。如果对“查禁职责”作广义解释,在“扫黑除恶”背景下,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负有查禁职责,包括上述国安警察、监狱警察、司法警察,包括公安警察中的其他警种,还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行政机关中的行政执法人员。
问:你是说,如果对“查禁”作广义解释,这些人都属于“纵容伞罪”的纵容主体?都可能构成“纵容伞罪”?
答:不,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恰恰相反,由于这些人承担的是政策性的查禁职责,而非法定的查禁职责,因此,即使他们不履行查禁职责,也只是不履行政策职责,而非法定职责,不可能构成“纵容伞罪”(但不排除构成“包庇伞罪”或其他职务犯罪的可能性)。同时,如果对“查禁职责”作广义解释,就应当相应地对“纵容”作广义解释,而广义的“纵容”并非“纵容伞罪”所指的“纵容”,不可能构成“纵容伞罪”。简言之,此“查禁”非彼“查禁”,此“纵容”非彼“纵容”,此“保护伞”非彼“保护伞”,不能偷换概念。
问:为何特别强调“行政执法人员”?有何深意吗?
答:其实也没啥深意。之所以强调“行政执法人员”,是因为与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人员相比,他们工作在第一线,依照法律、法规直接对具体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强制、稽查和处罚,而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因此,他们更容易接触、发现犯罪线索。一旦发现犯罪线索,他们就有将犯罪线索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法定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在“扫黑除恶”年份,他们就可能构成“包庇伞罪”,在其他年份,情节严重的,就可能构成其他职务犯罪(如《刑法》第402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同时,行政执法人员主要集中在建设、土地、海关、税务、工商、质检、药监、环保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正是违法犯罪活动的重灾区。可见,行政执法人员也是涉嫌“保护伞”的高危人群。
问:有此类案例吗?
答:有。公开信息披露,哈尔滨市呼兰区建设管理局原局长王明杰、环境保护局呼兰分局原局长樊大勇、国土资源局原局长侯玉、哈尔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原执行科科长侯立君等人,就因为涉嫌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犯罪线索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问:有判决结果吗?
答:暂无判决结果。
问:他们会被判“保护伞罪”吗?
答:两说。一方面,由于他们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包庇伞罪”的适格犯罪主体,如果确实包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他们就可能被判“包庇伞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负有法定查禁职责的主体,不是“纵容伞罪”的适格犯罪主体,因此,他们可能被判与“保护伞”相关的其他职务犯罪,但不应被判“纵容伞罪”。
问:如此说来,“纵容伞罪”与“包庇伞罪”主要有三个区别:一是“包庇伞罪”应当“利用职务便利”,“纵容伞罪”则无需“利用职务便利”。二是“包庇伞罪”需要有“包庇目的”,“纵容伞罪”则无需“纵容目的”。三是“包庇伞罪”的“包庇主体”包括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纵容伞罪”的“纵容主体”仅限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负有法定查禁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答:够专心+好记性。跟明白人沟通,就是省心!
问:“包庇故意”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想必“纵容故意”也同样存在吧?
答:是的,因此不再赘述。
问:关于“纵容伞罪”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包庇伞罪”的包庇对象和“纵然伞罪”的纵容对象是一样样的吗?
答:不完全一样样哈。“包庇伞罪”的包庇对象仅限于“人”(即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境外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而“纵容伞罪”的纵容对象包括“人”和“事”。
问:咋讲?
答:根据《刑法》第294条第三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就构成“纵容伞罪”,是吧?
问:是的。
答:可见,对纵容对象的完整表达应当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包括两层意思:其一,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即应当查禁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查禁,此可谓纵容了“人”。其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即应当查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而不查禁,此可谓纵容了“事”。易言之,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都属于“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问: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属于“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好理解。为何说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属于“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呢?
答:根据《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法定的犯罪组织,它的成立、存续本身就属于犯罪,因此,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可以理解为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进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基于组织与成员的共存关系,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当然就属于“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问:so that s ne!
答:你也别so that s ne了。关于本罪,你没有别的问题了吗?
问:没有了。
答:既如此,下面就简单聊聊广义“保护伞”吧。
四
问:怎么界定广义“保护伞”的内涵呢?
答:难界定。
问:为何狭义“保护伞”能界定,广义“保护伞”就难界定呢?
答:因为狭义“保护伞”是刑法意义上的“保护伞”,内涵稳定,故而可对其进行规范解释。而广义“保护伞”是刑事政策意义上的“保护伞”,内涵不稳定、弹性大,故而难以对其进行规范解释。事实上,至今为止,也没有哪个政策文件或法律文件对广义“保护伞”作过规范解释。
问:明白了。那广义“保护伞”总有个范围吧?
答:这个可以有。广义“保护伞”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狭义“保护伞”,也就是上面讨论的“保护伞罪”。第二类是狭义“保护伞”以外的其他“保护伞”,在此不妨称之为“政策性保护伞”。
问:“政策性保护伞”?怎么理解?
答:“政策性保护伞”是指虽尚不构成“保护伞罪”、但因为给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或“恶势力”提供了非法保护而必须予以惩处的“保护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其他职务犯罪的“政策性保护伞”,一类是构成违反党纪政纪的“政策性保护伞”。
问:“政策性保护伞”有何共性?
答:其共性是: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或“恶势力”提供了非法保护(包庇或纵容,下同),但这种非法保护又尚未达到构成“保护伞罪”的程度。
问:“政策性保护伞”与狭义“保护伞”有何区别?
答:区别有四。
问:区别之一?
答:充当“保护伞”的主体不同。充当狭义“保护伞”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充当“政策性保护伞”的主体则包括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含准国家工作人员)。
问:区别之二?
答:保护对象不同。狭义“保护伞”的保护对象仅限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政策性保护伞”的保护对象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
问:“政策性保护伞”所保护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和境外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吧?
答:是的。
问:“政策性保护伞”所保护的“恶势力”,包括恶势力犯罪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吧?
答:是的。
问:区别之三?
答:罪与非罪不同。狭义“保护伞”以构成犯罪(“包庇伞罪”、“纵容伞罪”或“保护伞罪”)为前提。“政策性保护伞”既可能构成犯罪(可称为“犯罪的政策性保护伞”),也可能只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可称为“非罪的政策性保护伞”)。
问:“犯罪的政策性保护伞”主要涉嫌哪些常见罪名?
答:三大类。
问:第一类?
答:第一类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问: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构成这一罪名?
答:当然。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本罪。
问:国家工作人员犯本罪也算充当“保护伞”?
答:你说呢?
问:想想也是。其一,瓜田李下,既然都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了,就免不了有意无意地提供这样那样的非法保护。其二,国家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但是对其所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直接保护,也是对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间接保护,更是对潜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无形保护。显然,这种非法保护社会危害性忒大。
答:深刻!
问:国家工作人员犯本罪的,怎样处罚?
答:最高法2000年《司法解释》第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本罪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犯本罪的,按一般规定处罚。
问:国家工作人员犯本罪的,可否同时构成“保护伞罪”?可否数罪并罚?
答:可以。因为这两个罪名之间既不是想象竞合关系,也不是法条竞合关系,不是实质的一罪,而是实质的两罪,可同时成立,可数罪并罚。正因为如此,《刑法》第294条第四款规定,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问:第二类?
答:受贿类犯罪。
问:主要就是受贿罪吧?
答:是的。
问:第三类罪名?
答:渎职类犯罪。
问:比如说?
答:比如说,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放纵走私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刑法》第九章规定的三十五个渎职类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
问:区别之四?
答:惩罚依据不同。对狭义“保护伞”的惩罚依据是刑法第294条,对“犯罪的政策性保护伞”的惩罚依据是刑法的其他法条,对“非罪的政策性保护伞”的惩罚依据则是党纪政纪。
问:区别之五?
答:处罚性质不同。狭义“保护伞”承担刑事责任,“犯罪的政策性保护伞”也承担刑事责任,但“非罪的政策性保护伞”只承担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
问:党纪处分包括哪些?
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条规定,党纪处分包括以下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
问:开除党籍就是“双开”中的其中“一开”吧?
答:正是。
问:政务处分包括哪些?
答:《公务员法》第62条规定,政务处分包括六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问:开除就是“双开”中的“另一开”吧?
答:正是。
五
问:通过上面这么一番抽丝剥茧,“保护伞”的出处、含义、分类、处罚都一一捋清了,但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答:大哥,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
问:咋讲?
答:咋讲?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首先,你的案件与“恶势力”有牵涉,但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无涉,这不就意味着不能定你“包庇伞罪”、“纵容伞罪”或“保护伞罪”了吗?这样一来,你不就彻底与狭义“保护伞”撇清了吗?
问:与狭义“保护伞”撇清啦?
答:是的。
问:那我能与“有罪的政策性保护伞”撇清吗?
答:能。
问:能?我受贿十八万元的事实可是清清楚楚啊!行贿人交代了,我自己也承认了,部分还有银行转账记录呢,这不就是所谓的铁板钉钉吗?
答:尽管如此,还是能与“有罪的政策性保护伞” 撇清,理由有二。其一,在案证据显示,你的受贿事实发生在2014年,那时“扫黑除恶”的政策还没出台呢。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不能用现在的刑事政策来评价你当时的行为。其二,行贿人不是本案的“恶势力”,本案的“恶势力”又没有行贿于你。简言之,就本案而言,你的受贿行为是孤立行为,与“恶势力”无涉。既如此,你就没有受人(“恶势力”)钱财替人(“恶势力”)消灾,那就谈不上包庇、纵容“恶势力”,更谈不上为“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了。
问:如此说来,真能撇清?
答:当然。不过,我所说的撇清,是指与“有罪的政策性保护伞”撇清,并不是指与受贿罪撇清。
问:这个我明白。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能与受贿罪撇清,毕竟已板上钉钉了。那我能与“非罪的政策性保护伞”撇清吗?
答:能。
问:也能?我为本案“恶势力”成员之一经办取保候审的事实也是清清楚楚啊!对方交代了,我也承认了,而且还有当时的被害人证言、验伤报告、和解协议等证据,也可谓铁板钉钉啊!
答:尽管如此,也应撇清,理由有三。其一,在案证据显示,你为本案“恶势力”成员之一经办取保候审的事实发生在2013年,而本案“恶势力”犯罪团伙形成于2017年。易言之,那时,本案“恶势力”犯罪团伙连影子都还没有。其二,虽然当时被害人构成轻伤,但当时的加害人具有自首情节且赔偿了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双方还达成了和解协议,加害行为又是因邻里纠纷引起,你为加害人办理取保候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因为加害人变成了本案的“恶势力”成员之一就否定当时行为的合法性。其三,你为本案“恶势力”成员之一经办过取保候审的事实发生在2013年,那时“扫黑除恶”的政策还没出台。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不能用现在的刑事政策来评价你当时的行为。
问:这么说,我就与“保护伞”彻底撇清啦?
答:是的。我不是一早就说过你不一定是“保护伞”吗?
问:既然我不是“保护伞”,为何又把我当“保护伞”弄进来?
答:怎么,觉得冤枉?大可不必哈。其一,你收受贿赂总是不争的事实吧?单凭这一条把你弄进来就不算冤。其二,“扫黑除恶”的“一案三查”要求有关。
问:什么叫“一案三查”?
答:“一案三查”中的“一案”是指黑恶势力案件,“三查”中的一查是指查办黑恶势力,二查是指查办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三查是指查办党委、政府在“扫黑除恶”中的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简言之,只要有黑恶势力案件,在程序上就必须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疑似“保护伞”(以下权且称之为“程序性保护伞),至于这“程序性保护伞”是货真价实,还是徒有虚名,查了再说。
问:什么是“程序性保护伞”?你刚才一直没提过这类“保护伞”啊!
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提“程序性保护伞”,是因为这类“保护伞”实践中确实存在(就像你一样),但又不知如何界定它。如果硬要有个说法,也只能这么说:“程序性保护伞”是指在程序上被作为“保护伞”立案调查/侦查但最终查明不属于实体上的“保护伞”的“保护伞”。
问:听起来咋那么别扭?
答:说起来就更加别扭!
问:罢了罢了。能举个例子吗?
答: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问: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答:明白了就好。关于“保护伞”和你的案子,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问:你从宏观上、微观上、纵向、横向把“保护伞”问题捋了个遍,又把我的案子说了个透,我没啥要问的了,只有最后一个问题。
答:请讲。
问:什么时候再来见我?
答:该见你时定会来见你。
问:再见。
答:再见。
-
什么样的行为构成诬告陷害罪?
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行为。
-
操纵证券市场罪通常情况下怎么判刑?
近年来,立法机关、执法机关持续依法从严治理、打击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犯罪行为,逐步构建起行政、刑事多元的追责体系,对操纵市...
-
醉驾罚金要在什么时候交?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判决时,强制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资金,对犯罪分子进行经济制裁的一种刑罚方法。
-
入室打人构成什么案件?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房子如果没有经过同意的话,其他人是不可以进来的,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如果还入室打人的话是...
-
未成年人怀孕男方该怎么判?
虽然现在的性观念比较开放,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未成年的情况下发生关系也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处罚,这需要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分析...
-
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是怎样?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犯罪既遂,是指犯罪人的行为完整地实现了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的事实。
- 共同犯罪应当具备的条件是什么2023-02-23
- 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些?2023-02-23
-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表现有哪...2023-02-23
- 抢劫罪的立案标准是怎样的?2023-02-23
- 因琐事持铁锤将人砸死,会受到...2023-02-23
- 贵州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被判无...2023-02-23
- 备案侦查与立案侦查关系是什么...2023-02-23
- 男子核酸检测阳性后谎报行程,...2023-02-23
- 防控新型肺炎期间,经营者违反...2023-02-23
- 刑事证据要符合什么条件,刑...2023-02-23
- 涉嫌非法集资1395亿,18...2023-02-23
- 管制对象有哪些?管制的内容包...2023-02-23
- 销售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劣药构成...2023-02-23
- 小三明知对方有家庭生孩子算重...2023-02-23
- 什么情况下才会免于追究刑事责...2023-0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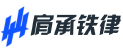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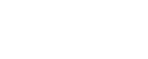
 扫一扫在线浏览
扫一扫在线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