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下留人!| 死刑复核程序四十年
作者:王建东
回首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争议、回归及回归后的不断完善,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随着死刑复核程序的日趋完善,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在不断提高。“枪下留人”真的可能会绝迹,最后成为历史与传说!
一
公元2002年4月29日,星期一,北京,东交民巷。
密闭的玻璃窗外,杨柳絮漫天飘飞,给人一种深深的压抑,几乎不敢大口呼吸。屋内,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的李**副庭长,正在收拾上一周刚换的办公室。白色电话机被孤零零的扔在办公桌一角,没有连接电话线,等待着后勤人员前来调试,地上则杂乱堆满了案卷和各种物品,整个屋子几乎已无落脚之地。
突然,一个不速之客推门而入,“李庭长,您好,我是西安的朱占平律师,现在有个十万火急的情况向您反映,请求对我的当事人暂缓执行死刑。”没等李武清接话,一份仅有768个字的紧急申诉也被朱占平双手递到了他的眼前。李庭长看着这位因爬楼而喘着粗气的律师,略一迟疑,又冷静下来,在逼仄的空间里,抓紧腾开一点地方,让朱律师坐下慢慢说。
2001年12月21日,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半年前发生在延安电影院通宵舞厅的一起伤人致死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董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为,2001年5月2日零时许,被告人董伟与多人酒后来到延安电影院通宵舞厅,因琐事与宋阳发生争吵并相互厮打,被在场的人劝开。后董、宋二人又在舞厅旁边的灯具门市部门外继续厮打,董伟用人行道上的地砖,向宋的头部连续打击致宋当即倒地后,逃离现场。宋阳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董伟对判决不服,他认为本案是被害人引起的,自己是被迫还手,不是故意杀人。于是,董伟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结果,陕西高院维持原判,同时核准死刑。董伟及其家属已经准备放弃了,但是作为董伟的二审辩护人,陕西西安的朱占平律师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为该案的死刑核准权已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朱律师决定4月27日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以寻求转机。4月28日,朱律师刚赶到北京,就接到董伟父亲的电话,说已经接到延安中院通知,将于第二天上午10点半对董伟执行死刑。情况紧急,朱占平只得临时调整方案,这才有了直闯李**办公室,请求暂缓执行死刑的一幕。从而也留下了至今仍被法律界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枪下留人”。
听了朱律师介绍的案情,又读罢申诉,李庭长也意识到了本案可能存在问题。他不敢耽搁,先组织人员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呈文,申请下达死刑暂缓执行令。然后拿起自己的手机,接通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的电话,并通过这位副院长得到了现场执行法官的电话号码。
“什么离执行死刑只差4分钟,我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电话的时候,连死刑犯董伟的面还没见到呢!”两个半月后,面对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延安中院法官任**对网上一些经过了演绎的说法不以为然。
九百多公里外的延安市看守所,警灯闪烁,戴着口罩的武警士兵手持步枪在车下警戒,等待将死刑犯押走行刑。楼内,负责执行死刑程序的法官任**、延安市检察院检察官韩**和另一名女法官正在对排在董伟前面的另一名死刑犯验明正身,10时24分,任**的手机响了。以下是二人对话:
李:“我是最高法院刑一庭,你是不是在执行一个叫董伟的案子?”
任:“是。”
李:“枪响了没有?”
任:“没有。”
李庭长立即说:“现在通知你,把这个案子推迟到下午3时执行,这期间我们会给你新的指令。”
任**追问道:“你是谁?”
“李*,武装的*,清白的*。开着你的手机,省高院杨副院长会给你们指示的。”
任**的第一感觉是怀疑其真实性:“咱和最高法院差得太远,根本没听说过有个李副庭长,等接到我们法院副院长的电话心里才踏实。
特事特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暂缓执行命令”很快就签署下来,这时,朱占平律师的手机响了,董伟的父亲在电话里放声大哭:“救下了!救下了!”
“李庭长,我为共和国有您这样认真负责的法官而自豪!”心情异常激动的朱占平紧紧握住了李庭长的手。李庭长说:“死刑案件剥夺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他顿了一下又说:“而且,我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敬业的律师!”
4月29日,朱占平心情始终难以平静。当他走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时,他决定在这里留个影,这一刻对他太重要了。
李、朱二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将对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变革,产生历史性的推动意义。并且在之后的岁月里,因这些变革而被人们反复提起。
二
“枪下留人”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全国反响强烈,近百家媒体纷纷转载,从而引发了对死刑复核程序的争议和思考。普通公众关注的是董伟这个死刑犯的命运,以及“枪下留人”式的戏剧性情节。而最高法院把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省一级高院,导致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名存实亡,则成了法学界诟病的主题。
死刑复核程序,是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所遵循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即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在经过普通的一审或者二审程序后,尚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还必须经过一个特别的复查核准程序。它的目的是为了在程序上多把一道关,防止错杀,坚持慎杀。由享有核准权的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报请核准的死刑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依法作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因此,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时,必须完成两项任务:
一是查明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据以定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罪名是否准确,量刑(死刑、死缓)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
二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并制作相应的司法文书,以核准正确的死刑判决、裁定,纠正不适当或错误的死刑判决、裁定。
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些特殊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没有《刑法》,又没有《刑事诉讼法》。司法机关的执“法”依据多是政策、文件,朝令夕改。公权侵暴横凌,下至普通公民,上至国家主席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以司法名义剥夺人的生命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情,死刑复核程序还无从谈起。
及至1979年,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高层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想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成文法律,完善法制。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分别于7月6日、7月7日以委员长令的形式将其予以公布。两部法律均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中,《刑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
第一百四十四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一百四十五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是中国法制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上述的这些规定,也宣告了死刑复核程序的诞生。按照这些规定,死刑都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死刑案件的监督,把好最后一道程序,防止冤杀错杀,当时的人们也对这一制度寄予了厚望。
但是在现实中,死刑复核程序的运作却并不尽如人意。
这一年,陕西人董伟刚满3岁,内蒙古人呼格吉勒图两岁。
由于80年代初期治安形势恶化,恶性刑事案件数量迅速上升,在《刑事诉讼法》仅仅施行了43天之后,1980年2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就通过决定,在当年部分下放死刑核准权。“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这一决定,成为死刑核准权下放的开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针对一个年份的决定,竟然持续了27年。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直接下放高级人民法院。延长了下放的期限。
按照1981年6月10日的决定,死刑复核下放的最后期限为1983年年底。但在那一年,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严打,使部分死刑核准权被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其中,允许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这两个决定,后来在法律界称之为“从重从快”决定。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规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依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
以从重从快决定为标志,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彻底下放给了地方。
后来,随着毒品犯罪的迅猛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1年6月6日、1993年8月18日、1993年8月19日和1997年6月23日,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和贵州等六个省、自治区的高级法院,对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经过这几波操作,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都被下放到了省一级高院手中。从死刑核准权被下放之初,法律界人士中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作为普通法律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作为基本法律的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产生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为期3年的第一轮严打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内部开始出现主张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的声音。1996年3月17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同时,1983年的从快决定被废止。修订后的两部法律均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人民法院组织法》与《刑事诉讼法》、《刑法》又产生了旧法与新法的法律冲突。但出乎法律界意料的是,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下发《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维持了原来的死刑复核中央与地方分工的格局。此时,距离修订后新《刑法》、新《刑诉法》1997年10月1日的正式施行只剩下最后5天。自那时起,关于死刑存废、死刑核准权回收的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学者意见不一”,某位刑法学专家说,“但在死刑核准权回收问题上,学界意见高度一致。”在实践中,死刑案件的一审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死刑后,被告人又有权利上诉到高级法院,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部分死刑案件来说,高级人民法院在行使二审审判权的同时,也行使死刑核准权,第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并为同一程序。对经过二审后仍然判处死刑的,高级法院经常在判决或裁定的结论部分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判决(或裁定)即为死刑判决(裁定)”。这样一来,死刑复核程序在高级法院手中被简略化、虚无化,完全流于形式,客观上导致了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
即便本身就是“枪下留人”案的二审法院,陕西高院刑一庭的领导在接受采访时也直言不讳:“立法程序上规定有复核程序,但最高法院授权给了省级法院,从体制上讲是不太合乎程序的,我们只能一套人马两套程序一起走,即便是内设机构也不可取。因为审委会最终只有一个。”“枪下留人”案成了推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一针催化剂。
★呼格吉勒图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一女子被掐死在公厕内。
1996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1996年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
1996年6月10日,19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距离案发只有62天。
200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成了案件复核组对案件进行调查。
2006年8月,复核得出结论,“呼格案”确为冤案。
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高院向呼格吉勒图父母送达立案再审通知书,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三
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不断暴露出问题,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引起全国法学界的不断争论和持续追问。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呼声愈发强烈,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2004年3月9日,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次表态,最高法院正在准备收回死刑核准权。
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表示要:“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落实有关法律的规定和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并制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司法解释。”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该法原第13条被删除。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
2006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公布,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过去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13条规定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一律予以废止。历时27年之后,死刑核准权终于彻底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收回不是工作的结束,最高法院陆续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完善。
2007年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院同日公告,该《规定》自2007年2月28日起施行。
2014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9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一批)的决定》,决定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于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明确保障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依法行使辩护权。
2019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这一规定,对于在死刑复核阶段,如何保障当事人、律师及相关人士的权利,做出了进一步细化的规定。
回首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争议、回归及回归后的不断完善,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随着死刑复核程序的日趋完善,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在不断提高。“枪下留人”真的可能会绝迹,最后成为历史与传说!
★追记
“枪下留人”案的最终结局并不是人们希望的那样。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全面审查,检查有关证人证言并反复讨论后,于2002年8月26日作出终审裁定认为,(董伟)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又无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之情节,故应依法严惩。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根据这一裁定,2002年9月5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暂缓执行令下达128天后,董伟被执行死刑,时年26岁。
终审裁定下达后,朱占平律师不再接受记者采访,不再对案件发表看法。他只对记者说:“我尊重人民法院的判决权,但保留自己的辩护意见。”
2007年3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执行大会,对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李树木公开宣判并执行死刑。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已公开的最早由该院核准的死刑案件。
2019年8月3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滴滴顺风车杀人案”被告人钟元依法执行死刑。
★作者介绍:王建东,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辞去公职前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多年,曾审理案件上千件,主要研究领域为合同纠纷、死刑辩护、审判观点等。
-
死刑的适用对象有何限制?
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生命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
-
男子在车管所刺死民警 一审获死刑,男子车管所刺死民警构成何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二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行为以及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的犯罪情节极其恶...
-
“弑母学霸”吴谢宇被判死刑后上诉,这类犯罪嫌疑人该不该做精神病鉴定?
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是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但精神病司法鉴定并不等同于免死金牌。吴谢宇作案的动机、手法和过程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
“南昌杀妻抛尸”案二审维持死刑,二审判决会出现哪些结果?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36条,刑事案件二审的结果有这几种:(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
-
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怎么办?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如果被告人有...
-
犯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吗?
犯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委托...
- 不服上诉有用吗2023-02-23
- 帮助别人自杀构成犯罪吗,法律...2023-02-23
- 死缓限制减刑能几年改判2023-02-23
- 为他人犯罪提供手机卡使用,会...2023-02-23
- 夫妻销售三无口罩获刑八年,还...2023-02-23
- 自首受害人已死亡的应如何追究...2023-02-23
- 身份证年龄与社保相符但与档案...2023-02-23
- 因家事纠纷放火殃及邻里房屋的...2023-02-23
- 暴力阻碍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23-02-23
- 酒后开车碾压路人,构成什么罪...2023-02-23
- 擅自冒领他人信用卡透支消费,...2023-02-23
- 故意伤害中的残疾赔偿金为何不...2023-02-23
- 孕妇贩毒可以免除刑责吗,孕妇...2023-02-23
- 信用卡诈骗罪可以减刑吗?信用...2023-02-23
- 做传销犯的什么罪名,严重会判...2023-0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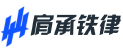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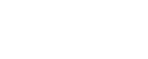
 扫一扫在线浏览
扫一扫在线浏览